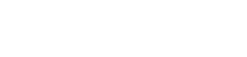



笔者所在团队近年来代理了多宗知识产权被害人委托刑事报案、参与刑事诉讼、民事索赔的案件,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之艰辛感触颇深。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多存在控告立案难、对被告人量刑轻、权利人索赔难等现象,导致大量侵权纠纷不能以刑事诉讼方式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而且,受限于刑事侦查的主客观因素、被害人提供司法鉴定检材能力、司法鉴定人员专业能力等因素,知识产权刑事诉讼裁决文书所认定的侵权事实、经济损失往往仅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而已,而这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在被害人后续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时仍然面临被推翻的可能。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办案经验,探讨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案件中允许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司法实务界的分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自颁布以来历经三次修正,但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规定的条件没有变化,其内容均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按照上述法条的规定,知识产权刑事诉讼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属物质损失的范围,依法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务界分歧较大的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15年1月19日废止)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述两个司法文件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作了限制性的解释,均规定被害人仅在“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两种情况下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故学界或实务界大多认为这是在司法解释层面上否定了被害人可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被害人对被告人或其他责任主体索赔,都需要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津01刑终779号案、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粤1322刑初777号惠州市霸曲电子有限公司、彭冬英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梁刑初字第330号刘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均认为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求不符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条件而裁定驳回其起诉。
但经检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3年1月1日)实施前后,都有法院支持被害人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诸多案例。在高级人民法院层面,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1)鄂知刑终字第1号熊四传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曾入选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陕刑终29号娄斌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内刑终28号杜聪斌、杜阳阳、杜建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王若飞、范志花、吕新年、张长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二审期间,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申请撤回民事起诉);在中级人民法院层面,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鄂05刑初40号侯运武、赵明宇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内07刑初58号程某某、于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基层法院的案例,有江苏省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新知刑初字第0008号陈某、凌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夏某、吴某甲、戴某、李某甲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陈某甲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镇经知刑初字第00001号韩某甲、韩某乙、韩某丙、韩某丁、潘某甲、倪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苏0681刑初11号徐某乙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豫1628刑初84号谷爱民假冒注册商标罪案等。
另外,笔者还检索到一宗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直接判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例,即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粤12刑终268号林锋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在该案件一审原审中,被害人曾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重审一审中,法院判处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二审予以支持。
程序分开之弊
知识产权刑事诉讼案件与被害人民事索赔请求分开审理,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病也显而易见。
一、浪费了司法资源,不利于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大多涉及刑民交叉问题,允许被害人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兼具有刑事打击与民事赔偿的双重司法保护功能,能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反之,则将存在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笔者办理的多宗侵犯商业秘案案件,被告人在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后没有可量化的违法所得,但被害人经济损失又客观存在,因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不得不在刑事诉讼结案后又另行提起多宗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据生效刑事裁决文书所认定的被告侵权事实、被害人经济损失金额来判令被告赔偿。此类民事诉讼的提起,权利人所提交的证据大多是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在指控时已举证过的证据,但民事诉讼案件原告、被告又需要再次对刑事诉讼中已质证过的证据再次举证、质证,承办法官也需要对刑事诉讼中已评判过的证据再次做出评判。作为原告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也需要因此而增加预缴诉讼费用、支付律师费等主张权利的成本,而且,因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仍可能存在一审、二审甚至是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再审等多个诉讼阶段,还将大大增加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张、实现合法权益的时间成本。
二、可能在民事诉讼中推翻在先刑事判决中关于权利人权利认定或经济损失认定的情形,损害司法权威性
2016年7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经过四年来的工作推进,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多已组建“三合一”审判团队,但大部分基层法院因各种因素限制而仍难以实施。为适应《刑法》对各类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定,绝大部分涉知识产权一审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且司法实践中存在多缓刑、多罚金刑的情形,很多案件因被告人不上诉而未出现二审程序,因此,对同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大多是由不同的审判团队作出。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对同一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事实在刑事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认定应当是一致的,不应存在冲突,但由于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审理重点的不同,不同的审判庭可能会对同一被控侵权行为做出相互矛盾的事实认定和判决,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案件相冲突的现象,尤其体现对在先刑事判决书审查认定这一问题上。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列为当事人的免证事由,但经分析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诸多裁判文书,综合来看,刑事判决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的拘束力仍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民事法官依然习惯于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进行考察,并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作出事实认定。笔者办理的一宗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生效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为1,535,941.29元,但在后续的民事诉讼中,一审法院仅判决被告(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二审法院则以被害人保密措施不严格且被告没有违法所得为由改判被告承担40%的经济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9月12日施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时,对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证据,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施行后,希望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列为当事人免证事由这一观念能得到法院系统的普遍认同,并在知识产权司法案件中尽量少出现刑民冲突的现象。
结 语
司法实践证明,知识产权案件重新犯罪率比较高,尤其在消费品行业,多形成了链条式、产业化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这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即国家花费了很多的司法资源,但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对知识产权违法犯罪人起到真正威慑的作用。笔者认为,除了犯罪利润率较高之外,也存在《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量刑偏轻、立案入罪标准偏高、权利人索赔时举证责任重等因素,即侵权人的违法犯罪成本相对较低。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条件作更为严苛的限制性规定,虽考虑了现实中各地法院审判力量的不均衡性,但也很诚实地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滞后性,未能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到与有形财产权利保护同等的高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修订司法解释,允许遭受物质损失的知识产权刑事诉讼被害人可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此程序的设立倒逼各基层法院对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积极推进,或者可另行出台司法文件,在一定时期内对部分案件特别复杂、专业性极强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一审可以由各地知识产权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其他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团队或商事犯罪审判团队审理。